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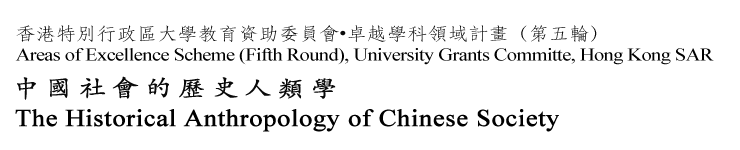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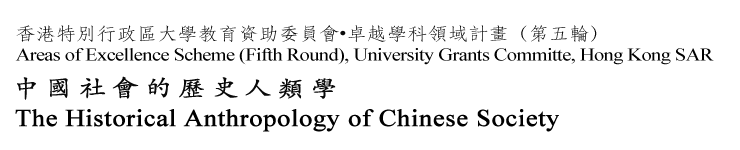 |
|
En 简 繁 |
| 江 西 |
|
|||||||||||||||||||||||||||||||||||||||||||||
江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鄱阳湖南岸的低洼地区自宋代以来就取得了迅速发展,而吉安和抚州地区则产生了大量的高级官僚。然而,书面文字的普及同样对宗教(道教)团体产生了影响,使得他们能够保存自己的文献,并通过师徒相授的方式流传。这个区域自宋朝以来出现的宗族习俗在明清时期新儒家礼仪向华南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江南地区和福建当地所供奉的对象也有部份来自该区域。 许真君信仰 (图,从左到右:西山万寿宫外景、西山万寿宫关帝殿、西山万寿宫高明殿(内景)) 唐宋时期,以西山为中心的许真君崇拜,经历了一个道教化的过程。唐代以前,许逊崇拜还只是一种家族性民间诸神崇拜。晚唐以后,随着地方性道教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以许逊为代表的净明忠孝道,西山万寿宫作为净明祖庭的地位得以确立。明代初期,由于政府对加强了对道教的管理,许真君崇拜和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一度受到抑制。但是,里甲制度的推行,又为西山万寿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至明朝中期,西山万寿宫这一神庙系统与里社祭祀有机结合,成为一种社区性的祭祀中心。加之官方宗教政策的转型和乡宦士绅的倡导,促成了明后期西山万寿宫的复兴。因此,西山万寿宫由净明祖庭向里社祭祀中心的转换,实际上是道教地方化、里社祭祀制度及以党正和士绅为代表的新兴地方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中期以后,西山万寿宫每年八月举行的“朝仙”仪式,吸引了全省数十县的民众前往参加。各地相继出现的各种香会组织,开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对西山万寿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晚清时期,西山万寿宫成为绅士、商人及香会组织展示其社会力量的地方权力中心。与此同时,随着各地万寿宫系统的不断扩展,至清末已形成以西山万寿宫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网络。 + 点击此处 了解更多关江西西部地区乡村社会所见万寿宫的历史 (图,从左到右:西山万寿宫香会会旗、西山万寿宫香会香头、西山万寿宫香会进香) 万载县 (图,从左上到右下:同治《万载县志》城池建置形势图、田下郭氏大祠(初建于天启七年(1627年),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先后重修)、高家祠堂(始建于乾隆至道光年间)、绿阴公祠(同治十三年(1874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修建)) 位于江西省西部的万载县,地当湘赣两省的陆路交通传统要道之上。其设县始于吴顺义元年,唐代时将县城从县境北部的罗城南迁至今址。明中叶开始,万载县城进行了城墙的修筑,城区范围也基本定形。1933年8月,《申报》记者陈赓雅路经万载县城时,就曾经对其“宗祠家庙,林立栉比”的景象留下深刻印象。截至今日,城区内也还保留大量宗族祠堂建筑。根据地方志、族谱,辅之以田野调查时获得的口述、碑刻等数据,我们基本可以梳理出一条从明后期开始,持续至民国时期,万载各姓宗族纷纷建祠堂于县城的历史脉络。这一层累迭加的宗族祠堂形成史,一方面与全县范围内的宗族发展历程同步,另一方面又凸显出其城区建祠的独特性。除了通常的联宗与助考等功能,城区的“隅籍”及其所体现出的“古户”的意义,成为吸引万载县各姓氏纷纷建祠于县城的主要因素。 +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关于江西万载的研究
(图,从左上到右下:宣三傩神庙(江西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宣三傩神庙正对面戏台、分布于各甲的族谱、与“十甲轮祀”有关的文字材料) “宣三”是一个“图”,它包括十个甲,各甲当中又有许多的家族与家谱。宣三这个“图”之下的十个甲轮流操办“宣三傩神庙”的祭祀,这被称为“十甲轮祀”。在宣三这个图的十甲中,每一个甲当中又都有一个至数个的社,十个甲共18个社,比如一甲就包括潭头汉溪社、涧埠陂坪社,这些社代表着每一个甲内的特定的家族和人群。每甲或社皆有地方保护神,即“福主“。例如:一甲潭头汉溪社福主仰山二王;二甲逢源泉塘社福主沈胜将军; 三甲宫江何古楼西社(土主庙)福主大帝;三甲上埠社太尉福主;七甲楼溪何楼溪社福主欧阳将军;七甲羊子山鲁家坊黄岭村花台社东岳大帝,玉角鹅王上将,社令真官;九甲石溪古楼金鸡社太子太保社令真官;十甲桥头(桥溪)永敬社福主桻梓大王。 “一图十甲”为组织形式的傩神祭祀活动,是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广东、福建移民进入该县以后家族发展、户籍编制,以及图甲户籍制度之下土著与移民在神庙祭祀中的具体表现。
(图,从左到右:吉安市吉安县永和镇清都古观、永丰沙溪欧阳修所撰泷冈阡表) 就许多层面而言 ,吉安地区在宋朝都是儒家新传统建立的核心区域。儒家传统的建立过程中,出现了一套为官方所认可的丧葬和祭祀礼仪,取代了佛寺在地方礼仪上的核心地位。 欧谱和苏谱同被视为修撰族谱的典范。但是在欧阳修葬母之时,实是以道观来看护坟墓的。宋代,以佛寺、道观或者庙宇来供奉祖先在华南地区非常普遍,而非祠堂。正如欧阳修同时代的人所指出,广为流传的欧氏族谱实际上被严重曲解。其实在的意义,需要在宗族制度庶民化的过程下,重新考虑。 +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关于吉安的研究
赣南上犹、武平、会昌等县
(图,从左上到右下:上犹县西昌乡学、上犹“门榜”习俗、营前黄氏族谱、武平岩前均庆院千佛殿中的定光古佛、水佛、新佛像、千佛殿的东边何仙姑亭中的两个何仙姑像、会昌杨公庙) 上犹县位于赣南西部,离赣州市区50公里,其县境西部地区即营前片区属于罗霄山脉,地势比较险峻,是明末清初广东移民进入比较多的地区,也是赣南土客冲突比较严重的地区,至今依然保留着比较浓郁的客家风情。 武平是定光佛信仰的中心,定光佛则是赣闽粤边界地区客家地区一个带有祭祀圈性质的地方神明,会昌也流行定光信仰。黄志繁教授关注定光信仰是为了探究客家早期历史。从已有的迹象看起来,客家早期历史与道教与佛教在当地传播有很大关系。 龙虎山
(图,从左到右:天师府内仁靖真人碑、天师府授箓院、张天师灵符)
龙虎山作为道教中心之一,唐代后期开始渐受重视,宋代成为江南符箓“三山”之一,元代主管江南道教事务,明清依然是全国道教的中心所在。今天,以龙虎山为中心的道教正一派仍然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图,从左到右:贵溪上清镇留侯家庙、贵溪汉浦倪郡公祠戏台、贵溪渐浦墩上唐司徒裔牌坊) 鄱阳湖区 (图,从左上到右下:江西省漳田河圩堤、江西省段家洲村土地庙、江西省都昌县康王庙、江西省都昌县渔村、江西省政府民国档案、草洲文契) 鄱阳湖区位于赣北,明清辖南昌、南康、九江及饶州四府。宋代以降,湖区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明清人口急剧增长,导致圩田、草洲开发及生态变化。这一历史过程中基层组织重组、圩神向宗族组织演化,并形成了湖区独特的小区政治格局。 瑞金县瑞林镇 (图,从左到右:瑞林镇村落景观、下坝村陈氏宗祠、保卫村陈公福主庙) 瑞金县瑞林镇十八个姓氏及其村落,从16至18世纪,都已建立宗族和创建了各自的祀典神庙,并合建了“(十八姓)启堂文会”组织,一套象征国家认同的乡村礼仪文化与地方自治组织由此形成。由于定居过程和各自历史条件的差异,这些家族村落在礼仪结构和力量发展上并不平衡。一个漕运军户家族在其中占据优势地位。18世纪以后,当地的生计问题突出,族群关系紧张。明清国家对这一地方社会的教化和整合并不成功,乡村礼仪文化的自主性发展反而留下了社会分化和族群冲突的隐患,为后来的中共革命造就了社会历史条件。 宁化县
(图,从左上到右下:宁化县河龙乡明珠村明末黄通所建大肚嵊山寨、福建省宁化县水茜乡宁氏祖堂、泉上桃窠庵妈祖神像前供罗祖画像、宁化县泉上镇“大明遗民九世祖李公世熊之墓”、清嘉庆畲族神像祖图手卷、福建宁化县曹坊乡滑石张氏祠) 明末清初,在闽北与赣东南的崎岖山地间“盗贼”蜂起,他们串联流窜、占山建寨、劫掠乡村、攻打城市,佃农和峒民是他们的主要身份。从明末至清初的几十年间,清朝势力的步步紧逼,南明朝廷的短暂统治,地方军事将领在抗清与反清问题上的反复,为佃农和峒民的“动乱”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明清官府、地方军事力量和由士绅领导的乡村社会力量都以不同的方式消解“贼寇”影响。与此同时,主导地方社会的士绅阶层在清初数十年间在效忠问题上受到困扰,他们中的一部份人被当时或后世的传记作者描述为忠贞的明代遗民,但他们更大的兴趣似乎在于解决地方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表面上他们最终都融入清朝,但他们的身份焦虑、认同危机和家国情怀都隐藏在他们所留下的文本中。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闽北宁化县及与之相邻的赣东南诸县的村落和城市,审视不同人群在从明到清的转变期间,如何运用时局以及他们所遭受的不同命运。 +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关于宁化的研究 |

|
||
| 版權所有 ©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 2013 香港中文大學 馮景禧樓221室,沙田,新界,香港 電話: (852) 3943 7158 傳真: (852) 2603 5685 Email: hisanthro@gmail.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