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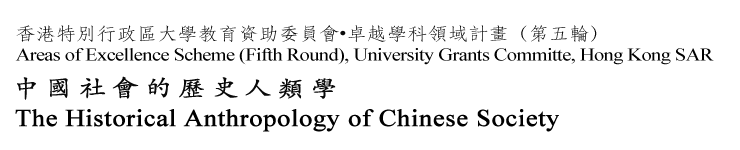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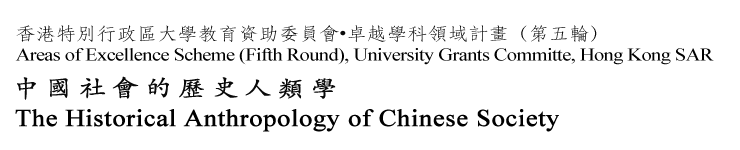 |
|
En 简 繁 |
| 浮生:水边社会之比较研究 | 
|
|||||||||||||||||||||||||||||||||||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中国的沿海、沿江、沿湖、生活着大量的水上人。这些人或被称为“疍”,或被称为“九姓渔户”,等等。这些称呼的背后往往交织着陆上人与水上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水上人很少掌握文字,撰写水上人的历史,往往采取陆上人的眼光。对一个文字记录一定很不全面的社会历史,我们可以怎样了解?
(图,自左上:濠江渔娘(钱纳利1774-1852),广东阳江东平港/贺喜 摄,水上人研究团队合影) 自AoE项目开展以来,对于水上人的历史感兴趣的十多位学者就致力于浮生社会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微山湖、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湖区,也包括了闽江、北部湾以及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通过比较,我们了解到,水上人社会的复杂与演变。 长期以来,王朝政府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水上社会的制度。主要依赖的是以税收为核心的河泊所以及对于船的登记。 杨培娜的研究说明:明代闽广河泊所设立之后,其维系多有困难,各地渔疍户纷纷逃亡,课额空悬。自正统年间开始就有大量河泊所被裁革,至嘉万年间,所剩无几。于此同时,渔课折纳征收,其方式和征收对象因时因地而异。总之,明代中期官员对于渔课征收的重点更多在于课额之保全,而不再也不可能拘泥于河泊所或由渔疍户来完纳。
明清鼎革之际,对于水边社会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是海禁与展界限。
谢湜认为,明清海島的遷遣和展界,是明清帝國面臨內外形勢對海疆經略進行調整和確立的曲折過程。明初至明中葉海島的棄守,與14-15世紀明帝國軍事、政治、經濟地理的變遷大勢密切相關。清初浙江海島的展復,伴隨著17-18世紀國家賦役制度及駐防制度的若干重要改革。一千年東亞海域貿易的長期傳統,以及浙、閩、粵海上人群的密集活動和遷徙,在清初海島展復後,造就了新的海域格局,影響了官方的制度重建和海島的社會重建。
关于身份的划分,“水上人”与“陆上人”是相对而言的。有人从陆上到水上,也有人从水上到陆上。也可以说,没有“陸上人”也就沒有所謂的“水上人”。當土地以及定居開始變得重要,水上人和陆上人的身份隔膜才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与凸现。比如珠江三角洲的历史就包含几百年来漫长的水上人上岸的历史。相信同时也有陆上人移到水上,虽然没有留下记录。
(图,从左到右:闽江沿岸的水上人/黄向春 摄、雷州企水港留恋于舟居生活的老妈妈/贺喜 摄、山东微山湖临湖而居/刁统菊 摄、太湖老兴隆社徐家公门/贺喜 摄) 除了舟居,还有寮居、棚居等 —— 既在水上,又在陆上的居住方式。 作为沙田开发和农业经营主要劳动力的疍民在已经开发成沙田的基围上搭寮居住。长久以往,逐渐形成了新的聚落小区。这种濒水为居的寮,处于基围上水陆之间,称为“水栏”、“蛋棚”、“草寮”,用几根木柱支持着,离地约一丈高,以防海潮淹没,内部间隔和船上差不多,可以说是从船演变而成的一种特殊住居形式,疍民的寮往往在当地自成一种景观。 疍民从“艇居”到“寮居”转变的初期,常常是“一叶破舟栖五口,日泊田头夜漂流”,但随着耕种沙田逐渐成为疍民的主要生计,“寮居”的疍民也逐渐稳定化。
(图:珠江三角洲寮居生活/曾惠娟 摄) 浮生社会如何维系社会组织以及传承记忆? 以香社为核心:太湖 演唱赞神歌是香头的职责,其他的成员或香客是无法取代的。唯独香头有资格演唱「赞神歌」,这很有可能就是香头权威的来源之一。 当「社」「会」的内部或与外部发生矛盾或对立时,由香头出面来处理或调解。作为渔民集团「社」「会」的头人,这应该是起码的职务。 另外从「神汉」「神职」来看,香头能通神或透过佛娘请「老爷开口」、擲四片「读兆」的牌子来确认神意、運用神明的力量为香客「看病」,凡此种种都是香头极为重要的职务。这些职能可以说正是香头们一代传过一代的能直接与神界沟通的特殊力量。 所有「社」「会」都有悠长的历史,都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尽管年代久远,但香头与香客们对香头的传承关系却了若指掌。香头的传承,基本上就是在某个姓氏范围里来进行,不是从香客里头去选,或由政府来任命。在香头传承上,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下一任香头由族里的哪个人来承接?如此而已。哪个姓氏的人家,具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能通神,香客的心里好像早就一清二楚了,因此他们很放心地交付给香头来主持各式各样的仪式。
神明的流转:湛江硇洲岛 硇洲岛的神明,从祭祀方式与地域范围之间的关系来看,都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驻庙神明,一类是驻家神明。 驻家之神轮祀的方式非常复杂,总体而言,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神驻于庙中,但是常常被村民迎请外出。在庙墙外,贴满了“预约”请神的请帖,这一类用红纸写成的请帖,当地人称作“标红”。 第二类神有庙却不驻庙,只有在节诞之期才回庙,平时就在村民家中轮祭。 第三类神没有庙宇,完全以轮祭的方式供奉。 对于整个硇洲岛而言,最重要的是四尊神,会主广福康皇、会主广福车大元帅、会主广德康皇、会主广德车大元帅。正月游神都是由他们开路,日子也由他们决定,其他的神则抽签决定如何排位。四位神都没有庙,在全岛范围轮祀,岛上只有这两个神的轮祀涵括全岛。全岛乡村分为六班供奉,每一班包括十余条村,每年轮一班。 总而言之,在庙宇内祭祀神明在当地不是历史久远的普遍现象,今天所见的庙宇,大多为近年新建。显然,这样的方式有利于祭祀群体内的整合。不过由于没有固定的地点,神明的历史更多地只能在口传和仪式的等非物质的层面保存来来。归根结底,硇洲岛的地方社会是以神祇的流转为核心来运作的,神随人走,神在哪里,庙就在哪里。
(图:轮祭于村民家中的上国平天侯王/贺喜 摄) 浮生状态或者刚刚上岸的水上人,是很少拥有大祠堂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宗族的观念,微山湖的续家谱、、北部湾的朝会都包含了当地人对于血缘谱系的表达。但是有趣的是,这些仪式的核心是神明,所以亦神亦祖的迭加非常明显。 山东微山湖:续家谱
所谓续家谱,最初其实并没有家谱,过去是只有当家族的辈分排行不够用了,才会在举行敬神仪式时,将下十辈或二十辈的排行公布出来,仅此才略可看出续家谱的含义。因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该仪式在渔民内部都被称作“敬神”,五年为“小敬神”,十年称作“大敬神”,基本都在湖上举行,借此机会各地的族人聚集在一起,了解近况,认识亲友,共同祭拜祖先和保护神。 届时,仪式以整个家族为单位,主家找来两条大船系在一起作为祭祀和表演场地,停靠在岸边,族人从四面八方驾船而来,带着自家的神像,供在大船船舱即神棚内,摆放香烛和供品,接受族人的供奉,仪式结束后带回家。 老祖并不是特指某一个神,而是一组神像,包括明堂、大王、唐神、师傅、菩萨等等。平时老祖居住在神龛,村民于腊月二十三把老祖“站”出来,送上天朝拜玉皇,叫送老祖。当天仪式结束后,将神像收起,放进神龛。六天后到腊月二十九接老祖。
(图:微村续家谱/刁统菊摄) 高州鉴江水上人:朝会 杨姓朝会一般于隔年的农历九月举行。进行朝会的坛是临时设的。 朝会开始前,陆续有村民将“太祖”从家里请来。他们请来的不是神主牌位,而是一尊一尊的小神像。杨氏“太祖”一共有38位,包括:余太君、穆桂英元帅等杨家将故事里的人物,杨六国老、杨三总兵、杨一尚师、杨三国老等杨姓的神明,还有一位如来佛祖。除了38位“太祖”,村民也把平日家里供奉的神像请来共赴盛会。在仪式的过程中,道士迎请了众多神明,道士请来的神用各色小旗代表。所以,杨门太祖朝会不仅是太祖们聚会,也是众神的聚会。村民请来的神像集中安放在坛外的长桌上,仪式开始后才依照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杨门太祖排位表”,一位一位按座次请上神龛。
(图:朝会/贺喜 摄) 在不同的渔港,水上人原本祭祀礼仪正在经历演变。有的人家开始用神主牌代表新近的祖先,也有人家用一块神主牌笼统地代表所有既往祖先。可以推测,这正是水上人上岸以后受到的陆上人礼仪和文字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上岸的水上人开始用宗族的法则来编纂谱系,界定人群。上岸改变的不止是居住的环境,也是社会的结构与文化。在此之前,从仪式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大堆的被认为是祖先的神明。虽然没有祠堂,也没有明确的谱系,但是供奉于船头、神龛的之上的各家各户木头公仔、小神或香炉就是与共同的拜祭仪式连贯着的,由此产生了可以代代相传的故事,可以年复一年延续下来的节日,也引发和维系着浮动岁月中群体的历史记忆与共同情感。
水边社会生产方式非常多样,除了渔业,还有运输、采珠、耕种、贩卖等等。加上,水面和田土又往往是互相转化的,因此时隐时现的水面,往往会成为争夺的资源,那么如何来确定对于水面的产权? 黄永豪的研究以洞庭湖为例,讨论在垦殖湖田的过程中,如何产生了大量的“渔民”。他认为,作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洞庭湖,号称为鱼米之乡,水产品产量占湖南全省一半以上。但是,洞庭湖近代渔业的发展却与洞庭湖自清中叶开始急速淤积有密切的关系。近代洞庭湖湖面积急剧萎缩,人们与水争地,反而造就了洞庭湖成为优良的渔业区,而围垦垸田却养育大量「渔民」,推动渔业发展。洞庭湖渔民小区的出现是洞庭湖地理变迁因素和国家政策下的“产物”。 张小也和梁洪生的研究则说明在争产的过程中,斗争的双方如何通过故事,说来历,来表达自己的权利。
(图:海南陵水新村渔港/贺喜拍 摄) 新国民,新渔民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步入了“近代化”的进程。商业化、城市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水上人”在地方社会的流动性加剧的同时,更加明显地与某些特殊职业、“水上保甲”等特定制度相连,从而使“水上人/岸上人”的分类标签持续性地获得了“近代”社会的意义。在这一背景中,“水上人”参与走私,谋生于夹缝之中,或游走于里社神祠与圣母玛利亚之间,操演着具有鲜明时代特性的“上岸”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水/陆”空间感被以“阶级”-“民族”为核心的新的国家制度的框架所打破,并与地方社会原有的权力话语交织并存,使“水上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困境;而这一状况的出现,一方面为“水上人/岸上人”的族群界线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认同的塑造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佐藤仁史对于浙江建德桐庐的九姓渔户进行了调查,他发现,自新中国成立前迄1960年代左右,九姓渔户只能过着一种“船上人”的船上生活;即便他们在陆上定居下来以后,与“岸上人”农民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仍止于粗浅之程度,从生活、通婚、职业等方面来看,九姓渔户仍然被放置在一种极端封闭的状况。此一事实显示:但凭雍正帝的一道贱民解放令,九姓渔户并没有获得“解放”,他们作为被歧视的对象,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存在,也毫不受到当代社会的关注。 另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九姓渔户对于自身作为九姓渔户的此一自我意识相当淡薄。这或许暗示出一事实:原来九姓渔户并不是来自自称,而是周围人们粘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相对于此,另有些人则接受自己是九姓渔户,他们将自身祖先的起源上溯至陈友谅及其部下之历史经纬,甚至有些人近来开始经营起了标示出九姓渔户的“渔家乐”。 |

|
||
| 版權所有 ©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 2013 香港中文大學 馮景禧樓221室,沙田,新界,香港 電話: (852) 3943 7158 傳真: (852) 2603 5685 Email: hisanthro@gmail.com |
||